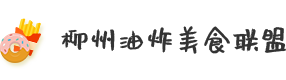拾麦
同兰辉╲
childhood
关于童年
童年首次关于拾麦的记忆,是在夜晚的煤油灯下。母亲坐在窑洞里的炕上纳着鞋底,不时的把针在头发上顺顺。我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,抄写着一篇《小猴子下山》的课文。记忆中,那篇课文很长,我连着抄了好几遍,母亲嫌我写那个“猴子”的“猴”的“犭”旁不正确,一遍又一遍的让我抄,我就不乐意了。母亲就开始给我讲:父亲小时候没东西吃,和奶奶一人胳肢窝夹几个编织袋,从三原柏社一路拾麦到朱村,脚上拖着没有后跟的布鞋……
Summer
夏天
阳光sun
◆那年夏天,收完麦子,骄阳似火的中午,父亲把麦子摊在场里。就着铝壶嘴喝了母亲提到场里来的白开水,抬头望望万里无云的天,转过头对我说:“走,拾麦走,拾的麦给你换西瓜吃。”
◆那时候我家年年到春夏交替的时候就没有了麦面吃,新麦在地里还没熟透,父亲就拿了钐镰或者扛着钐麦杆子去了地里,拣熟了的麦子一小片一小片的开始割,然后捆成捆,用架子车拉回来放到场里晒。因为没有麦面吃,母亲就把玉米面加点白糖,放到锅里蒸出来那种“玉米面粑粑”,一口下去,满嘴都是渣。那时候特别期待新麦上场,意味着马上就可以吃到可口的白馍。西瓜更是奢侈品,所以父亲一说,我马上跟在后面蹦蹦跳跳的走了。
◇ 其实家家户户地里基本上都没有麦子了,那时候口粮都紧张。麦收完之后,干不了重活的老人小孩就在收过麦子的地里捡拾漏到地里的麦穗。人家大部分都在早晚拾麦,因为有潮气,麦粒不容易掉,人也不热。父亲选择在中午,就是这时候人少,可以多拾点。父亲在前面拾得飞快,我跟在后面一步三歇。不一会儿,我就在后面磨磨蹭蹭的不肯走了,用手拽着父亲的衣角,父亲拖着我走……
◇ 回到家,母亲把拾的麦穗放在家门口地上铺开,用棒槌槌、簸箕簸、筛子筛,收拾净晒干,另外装个袋子,等着门上来换西瓜的。
Life
生活
新麦晒干,逢着大渠放水,母亲和邻居相帮着找来一口大锅,把干了的麦子倒进锅里,倒上水,用木棍搅,用笊篱搭,然后铺到塑料布或编织袋子拆开缝到一起的篷布上晒。那时候村里唯一的磨面机没有去杂质的那种功能,磨面前必须要用水淘一遍,去了杂质也方便脱皮。
终于可以吃上白面了。
母亲抓来一把麦秸,用火柴点燃了塞进灶膛。
火苗渐渐旺了起来,我在旁边拉着风箱,咣当咣当。潮湿的桐树枝“扑扑扑”的响着,一端燃着火苗,另一端冒着白沫和白烟;火苗舔着锅底又弯回来,犹如院子里那只高傲公鸡的尾巴。
“换——瓜——来……”门外传来卖西瓜陌生而又熟悉的叫卖声。所谓换瓜,因为农村那时候大都缺钱,但是麦子是自己种的,所以就把麦子折成钱,用麦换西瓜。如果是用架子车拉的,那就是附近的农人们种的西瓜。
“妈,外头换瓜哩。”我坐在灶火旁,边拉着风箱边说。
“换让人家换。”母亲低着头在案板上用擀杖擀着今年才磨的新面,头也不抬的说。
我噘着嘴,嘟囔了一声出去了。
门外大杨树下的阴凉处,戴着发黑的草帽的卖瓜的老人家蹲在地上,端着旱烟锅,正在吧嗒吧嗒的抽着,太阳透过树叶洒下一地的斑点,树梢上知了在“知了知了”刺耳的叫着,架子车上的西瓜又大又圆……
不一会儿,系着围裙的母亲用碗挖了几碗麦,装到编织袋子里,两只面手提着来了,一番称重挑选后,我跟在后面,怀里费劲的抱着两个大西瓜踉踉跄跄的回了家………
今年的夏收刚刚结束,那天外出回来,儿子趴在车窗上,吹着习习凉风,望着村外的麦地里弯着腰拾麦的人,问我那些人在干啥。我说在“拾麦”,儿子仰着头一脸诧异,“麦不是都收完了吗?”。于是我又开始给儿子讲父亲那时候拖着没有后跟的布鞋,弯着腰一路拾麦的故事……
时光荏苒,流水淙淙
80后的我已近不惑之年
父母大人都相继离开了我们
但是,有些事
有些话,有些场景
却时时回响在耳边,萦绕在眼前
给予我鼓励,鞭策我向前
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做人的道理
和生命的意义
比如拾麦
ღ
1980年12月出生于小丘镇朱村,从小酷爱文学,15岁开始在原《耀县文艺》发表第一篇诗歌《我们这代人》,自学考试“汉语言文学”专业毕业,退伍后辗转各地务工,2010年开始经营门店“同辉影像工作室”,从事婚礼摄像、后期制作;2014年12月担任朱村村委会文书至今。
编辑:冬青
带你发现耀州之美